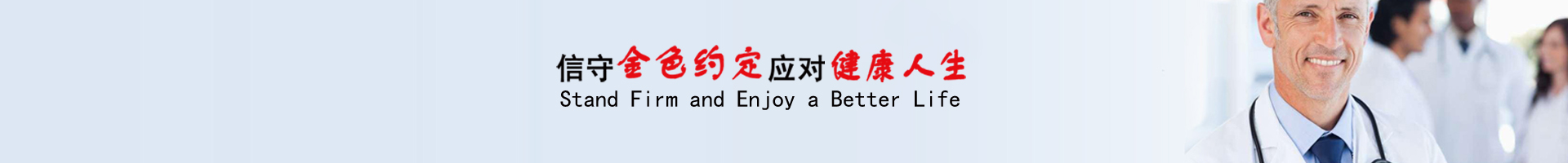【共識】骨折相關性感染定義的共識
2024-01-21瀏覽:
文章轉載于:中華骨科雜志, 2018,38(9) : 513-518
作者:Metsemakers WJ Morgenstern M McNally MA Moriarty TF McFadyen I Scarborough M Athanasou NA Ochsner PE Kuehl R Raschke M Borens O 謝肇 Velkes S Hungerer S Kates SL Zalavras C Giannoudis PV Richards RG Verhofstad MH 喻勝鵬(譯者) 孫東(譯者) 汪小華(譯者)
作者:Metsemakers WJ Morgenstern M McNally MA Moriarty TF McFadyen I Scarborough M Athanasou NA Ochsner PE Kuehl R Raschke M Borens O 謝肇 Velkes S Hungerer S Kates SL Zalavras C Giannoudis PV Richards RG Verhofstad MH 喻勝鵬(譯者) 孫東(譯者) 汪小華(譯者)
骨折相關性感染(fracture related infection, FRI)是創傷骨科一種常見的嚴重并發癥。迄今為止,尚無明確定義,因此很難對該并發癥帶來的影響進行準確評估和對現有的研究展開比較。為解決這一難題,在AO基金會的支持下,我們成立了一個由科學家和醫學專家組成的專家組,旨在對FRI定義達成的共識。
形成FRI定義的最初動因來自一篇系統性回顧文章,作者發現絕大多數骨折相關的隨機對照研究均無統一的FRI定義。基于此,作者在AO Trauma會員中展開了對于FRI定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必要性的全球性調研:在2 000多位外科醫生的反饋意見中,約90%的受訪者明確表示需要對FRI進行定義。在這樣的調研背景下,舉行了一次關于FRI定義共識的專家會議,并最終形成第一份FRI共識。
專家組圍繞FRI診斷的基本特征,將其分為確定性診斷和提示性診斷。確定性診斷分為4條:①瘺管、竇道或傷口裂開;②傷口流膿或術中發現膿液;③兩個獨立點深部組織培養標本或內植物表面標本發現同樣的細菌;④術中取出的深部組織標本經組織病理學檢查確認存在微生物。同時專家組根據FRI的臨床體征及輔助檢查,提出了一套輔助的提示性診斷標準。但這些提示性診斷只能表明感染可能存在,最后形成確定性診斷標準需要進一步提煉和研究。
本共識首先對FRI定義進行概述,然后對定義的每個部分和對應的臨床決策進行解釋。本次提出的FRI定義不能用于指導治療,只是為規范臨床醫生報道,提高發表文章的質量,并且本共識在今后的前瞻性研究中還需要進一步驗證和修改。
一、前言
由于目前對FRI無明確的定義,所以很難對其帶來的影響進行準確評估[1]。1996年,Arens等[2]在AO/ASIF增刊中提出:令人驚奇的是所有文獻均提到感染,但是有關于"感染"的定義卻不明確"。事實上,在最近的一項系統綜述中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只有極少數的隨機對照研究(2%)使用了現有的感染術語[3]。
由于目前對FRI無明確的定義,所以很難對其帶來的影響進行準確評估[1]。1996年,Arens等[2]在AO/ASIF增刊中提出:令人驚奇的是所有文獻均提到感染,但是有關于"感染"的定義卻不明確"。事實上,在最近的一項系統綜述中也發現了同樣的問題。只有極少數的隨機對照研究(2%)使用了現有的感染術語[3]。
FRI缺乏清晰的定義,類似于許多年前關節假體周圍感染所反映的問題[4,5]。如關節假體周圍感染和糖尿病足感染,由于近年來形成了共識性定義,情況才得以改善[6,7]。但一直以來,并沒有一項適用于骨折患者感染方面的共識。創傷外科醫生知道不論是關節假體周圍感染的定義還是來自于疾病控制中心的定義均不能直接套用于骨折感染病例。因此,形成FRI明確定義的觀點被最近一次針對于AO Trauma會員的全球性調查所證實。
在AO基金會的支持下,專家組成員就FRI定義達成共識。參考Cats-Baril等[8]制定關節假體周圍感染定義的過程,制定FRI定義共識經歷三個階段。①第一階段,依照改良Delphi程序[8,9],專家組成員通過視頻會議和郵件彼此廣泛交換意見;②第二階段,專家組成員面對面就第一階段形成的共識展開討論,對存在的問題和解決方案舉手表決;③第三階段,通過第一階段的意見交換,確立了針對明確FRI定義所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四個議題,分別是:分型、部位、術語和診斷標準。2016年12月,AO基金會在瑞士達沃斯舉行了第二階段專家共識的會議[10]。與會專家分別代表全球范圍的多個機構,包括AO基金會、歐洲骨與關節感染協會(EBJIS)和致力于FRI工作的各個創傷骨科醫院和學術機構。由于FRI需要多個學科的共同參與[11],所以此次會議邀請了感染疾病專家、創傷骨科醫生和臨床微生物專家參與討論。同時FRI相關領域的科學家也提出了一些意見。
會前,專家組提前對關節假體周圍感染的定義和其他一些骨科領域相關已發表的文獻進行了復習;在會議過程中,對前面提到的四個議題分別展開討論;最終形成了關于FRI的初步定義,并且隨后以文章的形式進行進一步解釋和說明。
二、FRI的定義
本文僅介紹骨折相關感染的共識,并未對感染進行分型,也未涉及具體的解剖部位,或者提供一整套的FRI術語和治療方案。這些問題均需要在今后去逐步解決。
本文僅介紹骨折相關感染的共識,并未對感染進行分型,也未涉及具體的解剖部位,或者提供一整套的FRI術語和治療方案。這些問題均需要在今后去逐步解決。
在既往已形成的關節假體置換術后感染的共識中,專家組認為需要通過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和影像學表現來確認或是排除感染[6]。這個辦法同樣適合于FRI。
專家組同意FRI的一些特殊臨床表現可以作為診斷感染的依據,這些特征應該在FRI定義中有更多的體現。而其他一些非特異性的表現僅提示感染的存在,因為這些特征也可能在非感染病例中存在。因此,確立診斷需要形成兩個不同權重的標準,即確定性診斷(只要滿足一個條件即可確定感染的存在)或提示性診斷(一些與感染可能相關但需要進一步明確的FRI特征)。
在專家組成員會議上,每條有可能成為診斷標準的臨床特征均被單獨討論。圖1是一個可供臨床醫生在日常工作(臨床和研究)中診斷和明確FRI的流程圖。

圖1 骨折相關性感染診斷的流程圖
(一)FRI的確定性診斷標準
1.瘺管、竇道或者傷口裂開(皮膚表面與內植物或骨相通)。
2.傷口膿性滲出或術中發現深部膿液。
3.術中由兩個獨立來自深部組織或內植物表面取樣點的微生物證實為同一種細菌。對于組織取樣,應當分別用清潔的器械至少取樣三次以上(不能取自于淺部組織或竇道的拭子)。關節鄰近部位的骨折存在有關節積液的情況,需要進行無菌穿刺以獲得單獨的一個培養標本。
4.手術中取出的深部組織當中,組織病理學檢查通過特異性染色發現細菌或者真菌。
(二)FRI的提示性診斷標準
1.臨床表現(任何一個)
·疼痛(不負重,隨時間延長不斷加劇,新發的)
·局部腫脹
·局部發紅
·局部皮溫增高
·發熱(口腔內溫度超過38.3 ℃)
2.影像學特點(任何一個)
·骨溶解(骨折端,內植物周圍)
·內固定松動
·死骨形成(逐漸形成的)
·骨愈合進程受阻(骨不連)
·骨膜反應(出現在非骨折部位或已愈合的骨折部位)
3.發現致病菌
術中深部組織或者內植物表面(包括超聲清洗液)的一份標本培養發現致病菌。對于組織取樣,應當分別用清潔的器械至少取樣三次以上(不能取自于淺部組織或竇道的拭子)。對于關節鄰近部位的骨折存在有關節積液的情況,可以進行無菌穿刺以獲得培養標本。
4.升高的血清炎癥標志物
對骨科創傷病例應謹慎解讀。血清炎癥標志物(紅細胞沉降率、白細胞計數、C反應蛋白)出現二次上升(特指在第一次升高后降低)或者一段時間內的持續增高,在排除其他原因所致感染的情況下可以認為是提示性診斷。
5.傷口滲出
術后數天新發的其他原因難以解釋的持續性不斷增加的傷口滲出。
6.關節感染
對新發關節積液的骨折病例,外科醫生需留意FRI可能存在于以下兩種情況所致的鄰近關節感染:①內植物穿破關節囊(股骨髓內釘);②關節內骨折。
三、討論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人們越來越多的注意到在已發表的文獻中缺乏對FRI的明確定義。一個很明顯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問題極為復雜。與關節假體周圍感染相似,FRI的定義應當包涵疾病的各種臨床表現。但FRI不僅涉及到許多解剖部位,同時還要包括不同的骨折類型、不同程度的軟組織損害、不同的宿主狀態(單發或多發創傷)。這導致用一個定義去解釋所有的FRI患者特征非常困難。然而如果考慮了所有FRI的基本特點和骨骼肌肉創傷患者的特征,用一個相對統一的定義去解釋絕大數的FRI患者的特征卻可行。由于現階段缺乏關于此類患者診斷和治療基本理念的科學證據,所以無法形成一個基于科學原理的定義。Cats-Baril等[8]提出:臨床實踐在許多方面缺乏科學證據,促使醫學界通過尋求替代辦法以尋求最佳解決方案。國際專家組成員形成的會議共識是其中的一個解決辦法。因此,對于FRI定義,專家形成的共識不啻為一個可行的方案。借鑒關節假體置換術后感染共識的形成過程,專家組召開了一次集體會議。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人們越來越多的注意到在已發表的文獻中缺乏對FRI的明確定義。一個很明顯的原因是因為這個問題極為復雜。與關節假體周圍感染相似,FRI的定義應當包涵疾病的各種臨床表現。但FRI不僅涉及到許多解剖部位,同時還要包括不同的骨折類型、不同程度的軟組織損害、不同的宿主狀態(單發或多發創傷)。這導致用一個定義去解釋所有的FRI患者特征非常困難。然而如果考慮了所有FRI的基本特點和骨骼肌肉創傷患者的特征,用一個相對統一的定義去解釋絕大數的FRI患者的特征卻可行。由于現階段缺乏關于此類患者診斷和治療基本理念的科學證據,所以無法形成一個基于科學原理的定義。Cats-Baril等[8]提出:臨床實踐在許多方面缺乏科學證據,促使醫學界通過尋求替代辦法以尋求最佳解決方案。國際專家組成員形成的會議共識是其中的一個解決辦法。因此,對于FRI定義,專家形成的共識不啻為一個可行的方案。借鑒關節假體置換術后感染共識的形成過程,專家組召開了一次集體會議。
盡管在FRI的定義及其組成部分的重要性方面專家組達成了共識,但仍有一些議題需要進一步探討,其議題圍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
(一)分型
既往許多分型根據FRI的不同分類劃分,如急性、慢性感染,或者早期、延期、晚期感染[1,12,13,14]。專家組關心的關鍵問題之一是:是否需要對FRI進行單獨的定義,或者FRI定義是否需要根據每個分型進行單獨定義(如急性和慢性感染)?在會議期間,專家組認為只需要一個FRI定義。
這個決定主要基于兩個重要原因:第一,再次分型會導致定義過于復雜繁瑣,增加了日常使用的難度。第二,現有的部分分型依時間而定,但這種分型并未基于科學證據。這說明有關FRI的定義均不夠深入和細致(如受傷的時間、出現癥狀的時間),且有一定的主觀性(如急性感染轉變慢性感染的時間為6周)。所有這些問題均給FRI的定義增加了難度[3]。專家組同意急性和慢性感染屬于不同的疾病狀態,需要不同的治療策略,這些均不影響對FRI進行統一的定義。
專家組同意在下一個階段中舉行類似的研討會,以達成關于FRI分型的共識和治療指南的共識。
(二)部位
在定義FRI的過程中需要解決的第二個難題是感染在手術部位或傷口內,但是卻要按照"淺表切口感染"的方式描述[3]。疾病控制中心在發布切口區域感染時,對淺表切口感染、深部切口感染和器官組織感染進行了區分[15,16,17]。Bonnevialle等[18]認為使用"淺表切口感染"具有很強的主觀性,在FRI當中使用會產生很多嚴重問題。細菌侵襲的深度只能通過皮下組織分離的標本進行評估。這意味著傷口分泌物拭子不能用于診斷FRI,每個感染傷口均必須暴露后,才能獲取需要的培養標本[18]。外科大夫在處置FRI時,病例均須暴露內植物和骨折端(如踝關節骨折)。如果培養結果是陽性,則可以診斷為深部感染。在一些與FRI相關的臨床研究當中,這些詞語(表淺和深部)的混亂使用,增加了文獻之間比較的難度。在臨床實踐中,感染的確定性診斷和提示性診斷已足夠提醒臨床醫生制定治療計劃。其治療的獨特性可能與感染特點有關(如淺表的蜂窩組織炎或深部的感染性骨不連),但這不是本次FRI定義討論的范疇。
與關節假體周圍感染不同,FRI中需要涉及許多解剖部位(如肱骨、脛骨)。盡管每個部位的特點不一致,但此次定義不涉及制定治療原則。若根據解剖特點對感染定義進行二次區分,會導致定義更加復雜且沒有必要。感染的診斷標準與解剖部位無相關性。
在會議當中,專家組一致同意不需要對FRI進行再次分型(如淺表或深部感染,某個解剖部位)。有些淺表感染并沒有與骨折和內植物相通(如蜂窩組織炎、釘道感染),這些詞語只是為了便于定義或資料收集。外科醫生只需明確是否存在感染,而無需考慮感染程度、部位和分型等問題。FRI中包含了淺表感染,但只能出現在回顧性分析中,而不能在治療指南中。考慮到解剖部位特殊性,今后制定治療指南可以考慮分型。
(三)術語
在既往的臨床研究中,有許多和FRI同樣使用的詞語(如創傷后骨髓炎、骨炎、深部感染)。通常情況下,骨炎和骨髓炎兩個詞語無區別。在英文文獻當中,臨床上使用的骨髓炎代表骨感染[19],但一些國家和地區FRI和骨感染卻代表的是骨炎。Tie-mann和Hofmann[20]認為骨炎和骨髓炎的主要不同之處是感染出現在骨表面的方式不同。骨炎通常指因細菌而引起的骨感染(侵犯從皮質骨開始),可以導致整個感染病灶骨的完全破壞。骨髓炎指始發于骨髓的炎癥,隨后波及到皮質骨和骨膜。臨床及相關研究發現這兩種疾病非常相似,且常難以區分[20]。在FRI當中,骨髓炎和骨炎均不能替換FRI的含義,因為FRI主要考慮細菌是否存在于骨折端和內植物周圍,而不是感染的發病機制。
研討會上,專家組同意在骨骼肌肉創傷患者當中使用更加標準且規范的醫學感染術語;同時提到在臨床研究中,應謹慎使用骨髓炎和骨炎兩個詞,因為二者很難通過臨床和臨床前研究進行區分[1],一些病例早期發病的原因可能并不是感染。
專家組認為需要使用覆蓋面更加廣泛的詞語。這個詞語應當包含感染、存在和不存在內植物的情況以及骨骼的各個部分(骨皮質、髓腔、干骺端等)。骨折相關性感染(FRI)是一個相對較好的詞語。專家組建議在今后便于統一,如對骨侵犯的程度沒有更加詳細信息(如組織病理學)加以描述的情況下,在骨折感染病例的臨床研究中應當使用FRI這個詞語。
(四)診斷
FRI的診斷標準是通過專家組逐一討論后決定的,其中有許多臨床征象和診斷方案被納入其中進行討論。毫無疑問,有些特征是在骨折端感染之后出現的(如病原學診斷,可以認為是感染存在的依據),另外一部分特征可能只是提示感染存在,但卻是由其他原因所導致(如提示性診斷標準)。因此,在設定FRI診斷標準時,應將其分為確定性診斷標準和提示性診斷標準。再次需要強調的是,此方案只限于診斷感染,不提供感染分型和治療建議。另外,設定提示性診斷標準是為了促進臨床研究,以尋求更多的確定性診斷標準。對提示性診斷標準舉個例子,如持續性、不斷增加或新發的傷口滲出需要進行深部取樣,以培養排除可能存在的感染,這是在清創手術中最常見的操作。
專家組認為有些特征可以直接作為確定性診斷標準,如竇道、瘺管、傷口裂開等。一旦出現這些征象則表明骨折端或內植物與污染的皮膚表面相通,細菌可經該通道達到骨折端或內植物周圍并引起感染,即便有些時候是非顯性感染。而其他一些局部的臨床征象(如疼痛、紅腫)被劃為提示性診斷標準。盡管這些征象具有主觀性,但在骨骼肌肉創傷病例中,軟組織覆蓋是一個重要因素,因此在定義FRI中需要認真考慮。
當定義某些診斷標準遇到困難時,需要被單獨列出進行討論。
由于描述FRI病理學的資料非常有限[20],所以專家組并沒有同意將組織病理學檢查作為診斷標準。其主要的原因是缺乏科學依據,特別是沒有可靠的診斷FRI的臨界值,以評估FRI手術中獲取的組織病理學標本在診斷感染時的作用[21]。臨床工作中,組織病理學結果以非客觀指標的形式出現,這使得臨床醫生很難做出決斷。如果病理學上中心粒細胞計數有可能診斷FRI,則其對骨折愈合和感染的影響還需進一步研究。最近一項關于組織病理學評分的研究方便了FRI的診斷[21],但此項評分還需要大量的臨床研究進行驗證。專家組同意通過對術中獲取的深部組織進行病理學特殊染色而發現細菌作為診斷感染的病原學依據。FRI定義只能囊括大部分的FRI,因此在一些特異性感染患者中會出現不適用的情況,如結核(抗酸染色)[22]和真菌感染(銀染)。專家組同意將這些特殊的檢查結果作為確定FRI診斷的指標。革蘭染色是診斷革蘭陽性和革蘭陰性細菌最常用的方法。但由于敏感性低,專家組認為只有在陽性的情況下才具備參考意義。總之,所有革蘭染色結果均需謹慎理解(有時可能只是污染)。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很多研究均嘗試采用分子生物學診斷感染,特別是在診斷關節假體周圍感染時采用聚合酶鏈反應進行檢測[21]。FRI相關的分子生物學診斷研究卻非常少。近幾年,只有一項相關研究,結果認為組織培養診斷FRI優于聚合酶鏈反應[21]。因此,今后還需要開展更多關于分子生物學診斷的研究。
在評估FRI患者時,影像學檢查非常重要,其原因不僅是為了尋找感染證據,同時是為了評價內植物松動和骨愈合情況。既往已采用各種核素顯像技術來輔助診斷感染。白細胞示蹤是該領域中使用最普遍的方法。不僅聚合酶鏈反應檢查存在缺乏針對于FRI的研究,白細胞示蹤檢查也存在著同樣的問題,雖然在骨髓炎外圍相關領域包括關節假體周圍感染開展了此項檢查,但這些研究均因不是針對FRI而無法將其納入到FRI的診斷依據中[22]。
由于缺乏有說服力的數據支撐,專家組一致拒絕將聚合酶鏈反應、組織病理學檢查發現急性炎癥細胞浸潤和核素顯像檢查(白細胞示蹤)作為FRI的診斷依據。專家組認為在長期慢性感染病例中,聚合酶鏈反應檢查、急性炎癥細胞浸潤、核素顯像檢查具備輔助診斷的意義,但在將其作為FRI診斷依據前須經過設計優秀的前瞻性臨床研究證實。
專家組成員們認為FRI的定義還存在許多局限性。如前所述,主要是由于FRI的研究非常少,這使得達成一個具備很強說服力的共識非常困難。但這不意味著專家組停止嘗試去形成第一份共識,以改進臨床工作。在收集基于此共識的研究數據以后,此共識可能會有相應的修改。另外,此共識只收集到非常小的專家團隊的討論意見。但是作為第一份共識,只邀請具備特殊背景知識的專家參與討論原因是考慮到最后達成結論的正確性。
四、結論
總之,FRI的定義是經過方案設計后逐步討論所形成。促成這項工作的主要動力是為了規范臨床醫生的報道,提高發表文章的質量。同時這項共識在今后,尚需要得到前瞻性數據的證實,目的是為了在臨床研究當中收集到實用性的證據。
總之,FRI的定義是經過方案設計后逐步討論所形成。促成這項工作的主要動力是為了規范臨床醫生的報道,提高發表文章的質量。同時這項共識在今后,尚需要得到前瞻性數據的證實,目的是為了在臨床研究當中收集到實用性的證據。
選自Injury, 2017 Aug 24. pii: S0020-1383(17)30563-6. DOI: 10.1016/j.injury.2017.08.040.